终生难忘的创社经历
——朱红东访谈录
采访人:房梦蝶
受访人:朱红东
时间:2021年12月8日
采访形式:线上
采访者:朱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您能给我们说一说你们大家当时创办银杏文学社的初衷是什么吗?
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进大学的时候,从77级到81级五级同校,那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年代,一方面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另一方面,作为位于祖国西南的云南边境一线,仍然在进行着边境防御作战。一方面祖国从被封锁、压制中打开国门,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另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大学生们同处一室,共同接受教育。以81级为例,班上有下过乡、上过班的老大哥、老大姐;有参加过前几年高考落榜,又重新考上的历届生;也有和我一样应届考入大学的学生。我上大学时刚满16岁,但因长得“着急”,曾被一校工认为是班上岁数最大的学生。为此,我专门写了一首诗,用以自嘲:我生下来就老了,然后又重新年轻……。我其实是带着文学梦进入大学的,自媒体时代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邮递时代的局限,时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当时,电视尚未普及,电话是脉冲式的,没有直拨电话,长途电话都要靠总机转接。听广播、看报纸、看杂志是获取资讯的主要途径,一首诗、一篇报告文学或小说都会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产生全面的影响。比如当时徐迟先生写的《歌特巴赫猜想》,让多少人了解到数学家陈景润的事迹,鼓舞了多少人的学习欲望!文章千古事,得失寸草心,文学在当时绝对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存在,自己的名字被排印成铅字,绝对是我梦寐以求的事,进入中文系不喜欢文学是很难想象的。其实一进入大学,有相同梦想的同学就迅速聚集在一起,交流、沟通、相互借鉴,读了一本什么书,看了一部什么电影,都在一起交流,兴致勃勃、乐此不疲。上一年级的时候,热爱文学的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活动,早就在班里形成了文学社的初型。创办银杏文学社就成了水到渠成、一拍即合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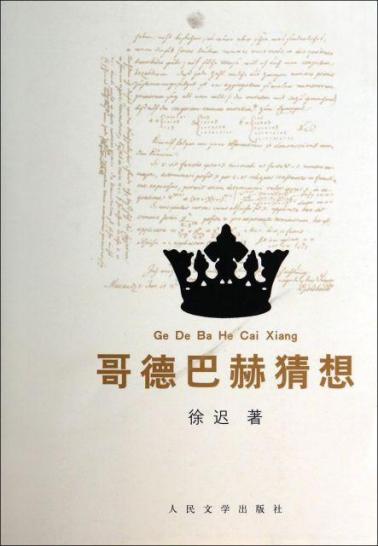
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图片源于网络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ipn=r&ct=201326592&cl=2&lm=-1&st=-1&fm=result&fr=&sf=1&fmq=166778720》)
采访者:“银杏”文学社这一名称是怎样诞生的?有没有特别的寓意?
朱:记忆印象之中,1983年秋季开学之后的一天,我在会泽院的阶梯水坛边遇上于坚,他问我:你是八一级的朱红东吗?我说是的。其实当时我已经认识他,记得他在学校壁报上刊发的一组关于老圭山的组诗,气势恢宏、极富感染力,心里早已经有结识他的想法。我在学校属于愿意做事的人,从大一起就出任学习委员,与老师和同学多有交往,也乐意为大家服务,干得最多的事就是帮老师搬家、买蜂窝煤等事。喜欢唱歌、喜欢踢球、喜欢诗朗诵、喜欢学校的一切。与高年级的师兄一起搞文学,那真是梦寐以求的事。于坚问我说,想不想一起搞个文学社?我回答道:太想了!于是,我和于坚分头联系了各自熟悉的同好者,大家多次聚到一起,讨论成立文学社的各类事宜,大家一致感觉到:不搞文学,学校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很快,八零级于坚、韩旭、姜大才、德明、李洪涛等,81级蔡毅、陈建华、赵小晋、叶向东、刘建国等,82级有张稼文、文润生、钱映紫、郭文平、田勇、高雄飞、杨黎坚、杨林青等,之后又延招至83级、84级。成立文学社自然要起一个社名,大家七嘴八舌说了许多社名,记得讨论社名是在云大银杏树旁的草坪上,记不清是谁提出的,就叫银杏文学社吧!当时校园里那两排高大的银杏树正要开始变得金黄,有同学说:银杏树从冰川四世纪生存致今,拥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还有人说:银杏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文学社的名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采访者:请问您还记得是谁最先提出想要成立一个文学社吗?文学社成立之前,您们做过哪些筹备工作?
朱:成立文学社可以说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成立文学社自然要得到学校的支持,当时的学校不设院,是校管系的体制,我们专门向中文系递交了成立文学社的请示,言明了成立文学社的目的、意义、宗旨。与此同时,一边分别拜访教授现当代文学和写作课程的先生们,寻求支持;一边联络热爱文学创作的各级同学。我当时是系学生会的学习委员,经常与各级的同学联系,也经常与校系各部门的老师们有工作接触,成立文学社的类杂务,主要是由我和张稼文等同学去办理的。申请递交上去很久,不见回音,大家都感到郁闷,记不得谁提议的,说应该去找张文勋先生,看看先生的态度。于是,一个夜晚,于坚、张稼文和我一起去到了张先生家。记得当时张文勋先生住在云大东一院的五楼一套单元采访者里,先生见我们来访,十分和蔼地把我们让进家里,亲切地招呼我们入座。我是第一次到访一位教授家,只见书采访者四壁排放满了书籍。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先生回答道:中文系的学生热爱文学,成立文学社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们!先生还谈到,他年轻的时候也热爱文学创作,曾经发表过散文、小说和诗作。知道先生的态度,我们简直开心得要命!当时,文勋先生任中文系主任,有先生的支持,成立文学社的所有障碍便一扫而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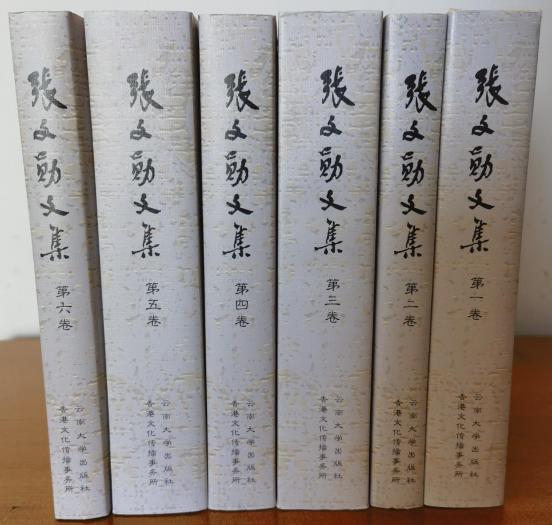
《张文勋文集》,yl6809永利官网出版社2000年版。(图片来源:王云杉提供)
采访者:银杏文学社成立之初,《银杏》杂志的主编们是如何确定每一期要刊登的内容的?是面向全校师生组稿还是社员相互推荐(或其他方式)?
朱:文学社成立之初是没有杂志的,我在学校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一块大黑板,然后约同学把它移放到校园的银杏树下,作为发表作品的“阵地”。社员们创作的好作品共同审定后,由于坚、王德明、蔡毅等字写得漂亮的同学抄到大白纸上,我们又将其粘贴到黑板上,以这样的形式刊发作品五六期后,才开始编发油印杂志。记得第一次傍晚布置好作品后,第二天跑去看反映如何时,看到有不少老师同学驻足在大黑板前阅览,心中别提多高兴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黑板也成为银杏文学社发布活动公告的阵地。
采访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成立银杏文学社之后其他社员的创作是否会影响到您个人的写作习惯、风格?
朱:我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期开始文学创作的。成立文学社之后,其他师兄弟的创作当然会影响到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其后大家一度十分认同的红土高原诗风格,就充分体现了生长在云南的诗人们共同的情怀。
采访者:当时文学社也经常会有校外的人员来参与活动,例如周良沛先生等,这些校外人士是如何得知银杏文学社的活动信息的?校外人员入社的情况多吗?是不是说当时文学社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朱:文学社组织活动当然有校外人员参加,如周良沛先生等社会知名人士参加活动是我们邀请来的,我们上门邀请过晓雪、周良沛、张永权、张长、米思及等先生。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些先生们只要邀请到,都非常乐意参与活动,不提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什么报酬,均按时来参加,并掏心掏肺、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交流体会、畅谈心声。活动主要的通知形式是粘贴海报,广而告知,欢迎校内同学参加。同期,昆明的各所高校也先后成立了多个文学社团,特别是云大周边的民院、师大、昆工、昆医几个高校文学社团交往频繁,有些活动也会邀请这些高校文学社团的同学们参加。我任社长期间没有接收过校外人员入社,当时定位的是yl6809永利官网中文系银杏文学社,随着文学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外系的许多同学纷纷要求入社,也积极参与文学社的活动。为了名正言顺,到了1985年,我和张稼文一起去找史宗龙先生,请求学校批准把银杏文学社升格为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史先生当时任yl6809永利官网党委宣传部部长,先生抽着烟耐心地微笑着听完我们的请求,便一口答应了我们所请,并十分难得地批给我们经费50元,用于开展活动。50元当时是一笔不少的钱,抵得上两个月的生活费,先生的支持,真让我们喜出望外。
采访者:您身边有没有不是银杏文学社社员的同学,比如您的室友,他们这些社外人员当时是怎么看待文学社的?如果方便,也希望朱老师能提供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
朱:我的同学现在还在云大任教的就有木霁弘、王卫东、秦臻、敬蓉、张秋红等几位不是文学社的,你们都知道这些教授,可以去向他们了解情况。
采访者:当时大家会不会借着文学之名开展一些联谊活动?您能和我们讲一讲当时你们的交际生活吗?在您看来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朱:借文学之名开展联谊活动?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请原谅我的过激!因为联谊这个词触碰了我的神经,时间过去了近四十年,没想到我还是那么敏感。当时就有一些流言说我们成立文学社就是为了方便谈恋爱,这个话题现在很美好,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正常、非主流、上不了台面的,此论一旦成立,文学社就会被解散,后果很严重。为此,我与稼文等同学商定,在文学社定下纪律,本社同学不准谈恋爱!共识之下,文学社搞任何活动,绝无谈情说爱的任何景象,主要的场面都是热烈地讨论着关于文学的人和事,创作风格、流派,古代的和西方的,省内的及省外的。现在想想,因为我们的坚持,文学社得以顺利成长;也因为坚持,也斩断了可能会很美好的的情缘。我认为我们当时对文学的热爱是真诚、纯粹、不含任何杂念的,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文章千古事、得失寸草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学在心中的地位绝对是庄严而神圣的,后来所谓的文青、文学流氓、撒娇、无赖、无病呻吟等文艺现象绝对跟我们没有一丝一毫关系。中国古代其实文史不分,文学其实也是史学,史学也可以称之为文学,如司马迁的《史记》。开展活动就是在开展与文学的相关的交流活动,坚定而执着,充满着理想的境界。
采访者:我们在整理银杏文学社资料的时候了解到,当时您们在东二院宿舍里面开了一个咖啡馆,作为“银杏文学沙龙”,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如沙龙的经费来源与使用、举办日常活动的流程、内容等
朱:文学社的各类活动开展起来之后,大家觉得应该在宿舍区搞一个文学沙龙,一则便于同学们课余时间交流;二则想通过经营活动,赚得一些钱,解决文学社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家很想做成此事。我打听到东二院二栋一楼的活动室正空闲,当时由校学生会掌管,我便找到时任校学生会主席的计义同学(云大历史系82级同学),请校学生会把活动室交给文学社搞文学沙龙,计义满口答应,随后就把活动室的钥匙交到我手上。沙龙地点有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坚找到书法家题写制作了一大块“银杏文学沙龙”的牌匾,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就把沙龙布置出来,我的高中同学、中文系83级的熊伟(银杏文学社第三任社长)很愿意张罗此事,便把他任命为经理,负责经营沙龙。沙龙开张后,每到夜晚时分,沙龙内座无虚席,周良沛、严婷婷、晓剑等知名人士,以及学校的部分老师来此与同学们交流文学,探讨问题。在后来的日子,由于各路文友不拘小节,喝咖啡不给钱,熊伟为人大气仗义,高兴不高兴都免单,沙龙经营便陷入困境,入不敷出,支撑不下,大约一年左右只好草草关张。题外话,我2004年到复旦大学进修,在校园中见识到由学生经营管理的超市、咖啡屋,生意兴隆,招募了许多大学生从事勤工俭学工作。好奇之下进一步探究,了解到复旦大学学生社团开展经营活动的时间晚于云大近一年,但其经营管理得越快越好,既为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又历练了经营管理的才干,一举数得。反观我们最早的探索,起了个大早,最后却不了了之。这大概就是地域文化的差异之处吧。
采访者:之前采访于坚老师,他说到当时文学社还会和西藏、重庆的一些高校有交流活动,您当时有参与过这些交流活动吗?(当时大家都通过什么方式交流?)您还记得具体有哪些高校吗?
朱:当时与省外高校的交流主要靠信件,通过写信交流、探讨文学问题,相互交换自办油印杂志,征集稿件。与多所高校的同学都开展过此类活动,记忆中我与重庆大学的燕晓东经常联系,他主编的《中国大学生诗报》还刊发过我很长的一组诗,但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此类文友还有很多,只知其名,多次联系,却从未谋面。
采访者: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社员们的作品一般都发表在哪些刊物?作品发表后,文学社里会组织什么庆祝活动吗?
朱:当时的文学期刊不算少,但要公开发表作品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一个创作者大约都经历过无数次投稿,要么是被退稿,要么是石沉大海。即便是退稿,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编辑本人手写的退稿信,简要指出文稿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加以勉励;另一种是铅印好的退稿信,手写部分只有退稿的日期,退稿也体现温度。当时昆明的文学期刊有省文联主办的《边疆文学》、昆明市文联主办的《滇池》,北京的《诗刊》、兰州的《飞天》等等,都是当时(我们)经常投稿的刊物。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飞天》办有大学生诗坛,在全国大学生心中极具影响,大学生诗人们都以在《飞天》发表作品为荣,创作出自以为好的作品首先都投往《飞天》,相信很多大学生诗人都接到过诗歌编辑张书伸先生的信。另外一类发表就是当时编印的各种内刊。作品发表后,也就是大家相互赏读,不搞什么庆祝活动。主要区别是公开发表的作品有稿费,内部发表的没有。1983年冬天,昆明下大雪,80级的师兄李洪涛在《丑小鸭》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我们几人约着洪涛兄在大雪中去探访筇竹寺,一路之上,插科打混,相互调侃,憧憬着未来创作出不朽的作品。下得山来,师兄高兴之余,拿出稿费请大家好好搓了一台。

《边疆文学》杂志(图片源于网络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ct=201326592&tn=baiduimage&word
采访者:您毕业以后还坚持写作吗?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使您中断了写作?
朱:我毕业之后做了8个年头的文学编辑,因深知创作之艰难,总是认真阅读来稿,生怕错过一篇佳作,绝不敢“草菅稿命”。同时,也业余进行着写作。广义上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彻底离开写作,可以说都是靠写东西工作、生活,只是从所谓诗歌、散文、评论等纯粹的文学作品延伸到其它领域,比如撰写过云南地下党的历史,策划过大型革命传统教育展览,以及撰写各类公文等等,没有一天离开文字。
采访者:您觉得加入银杏文学社对您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朱:不能说是加入,而要说“创办”,这样才准确。我是银杏文学社的几个主要创办者之一,其实创办银杏文学社对个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当时在系学生会任职,不搞文学社的话,我会成为学习生会主席,毕业分工的时候,可能会分到一个更利于成长的单位。但为了文学社,我辞去了学生会的职务,另外推荐其他同学去任职。当时,学校的不少同志,难免对搞文学社有不同的看法,分工的时候自然受到了影响,而当时对文学社关怀备致的张文勋先生已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环境产生了许多变化。创办文学社可以说对我个人产生了一辈子的影响,但如果能再选择一次的话,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去搞文学社,那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激情的人生,难忘的经历,难忘的岁月,难忘的友情,足以资养人生、宽慰灵魂。

银杏文学社首届社员合影(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采访者:您能说说当时和您一起的银杏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吗?大家还在创作吗?
朱:我与一起的银杏人保留着一辈子的友谊!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们,当初的一批银杏人不论是否还在创作,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均成为了各个行业的行家里手,担当着社会、单位、家庭的重任,坚韧守正,默默奉献。文学说到底就是人学,一颗对美与丑、善与恶、人生百态、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深刻洞察的心很难滋长邪念,大家都在用自己的脚步创作自己的人生,基本上都成为各个领域受人敬重的人。
采访者:您想对现在仍在坚持创作的“银杏人”说些什么呢?
朱:伟大的时代,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在关照好人生的同时,唯有坚持、坚持、再坚持……不管结果如何,关键的是努力的过程最精彩。当然,也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对待事业,实在走不通创作之路,也可以换条路走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应该不会过时。
采访者:感谢朱老师耐心、细致的回答,疫情之后,欢迎朱老师常回来看看。
朱:非常感谢你们的采访,让我有机会有一次回望过去。时光总是来去匆匆,不
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年轻时体会总是不深刻的,现在总算感受到了岁月的无情,人生没有如果,选择就要笃行。有机会能回到母校交流肯定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我感觉仿佛从精神层面从没有离开过学校,母校给我提供的教育是深入骨髓的,我从一个乡镇长大的孩子有机会来到极富底蕴的母校接受教育,在校园接受到的东西,影响了一辈子。例如张文勋先生的淡定、从容、宠辱不惊的大气;已远去天国的武显璋先生生前与我保持的深深情谊;赵仲牧先生的才华横溢;陈红映先生的激情澎湃;吴进仁先生的博闻强记;殷光熹先生的沉著幽默……一切的一切都雕刻在记忆深处。
“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校训,“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精神,师生、同学之间的情分,就是人生中火塘,温暖和慰藉着身心,激励着勇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