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
——黑红兵访谈录
受访者:黑红兵
采访人:林娟,骆维
时间:2022年1月2日3:00-5:00
地点:昆明市同德广场麦隆咖啡店
林:您是中文系83级文学社的,银杏文学社当时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您印象中当时的银杏文学社是怎么样的?
黑:实际上,那个年代有那么一个文学社,有它的一个时代背景:80年代初的时候,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以后,改革开放。当时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迎来了一个春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像其他领域一样,文学界也十分活跃。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为什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会出现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文革结束初期很年轻的一些人,经过十年文革,他们对社会、对人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然后就把他们的一些理解、感受诉诸于文学创作。应该来说,那个时代,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激情燃烧的那么一个时代,也是一个“诗”的时代。那时候大家在一起读诗写诗,当时这种情况在大学里是很多的。中文系有那么一波心怀文学梦的人,当时是比我年长将近十多岁,跟我们是差不多是在一块在学校里面。中文系有一些经历过下农村、进工厂,或者当过兵的同学,他们搞创作,也搞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诗人于坚。于坚是80级的。应该说那个时候,诗还是年轻人比较接受的,大家都在认真的搞创作。大约是在1983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我们的一帮同学,我记得大概十三四个人吧,80级的有于坚、吴丹、姜大才,81级的有朱红东、蔡毅,82级的有钱映紫、文润生、张稼文、杨林青、杨黎坚,好像他们这个班多一点,我们这个班大概是有我和潘先银。我们从云大出来走路到了北站,坐9路车到了烟厂那儿下去,下车我们就一路爬上山去了。在山上大家也比较激动,后来他们几个老写诗的同学就说,咱们以这一拨人为基础成立一个诗社吧。云大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物理馆旁边那一条银杏大道,就有同学提议叫“银杏诗社”。后来,大家商量叫诗社是不是太受局限了,因为诗它仅仅就是一种文学形式,我们就把它改成了文学社。银杏文学社就是这么来的。回来以后,实际上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要成立一个什么社团组织还要去登记什么的,那时候没有。我们大家经常在一块朗诵,主要以诗为主,包括舒婷等一些著名作家的,也可以朗诵自己的诗作。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应该有个载体,当时系里面的老师们、领导们也比较支持,我的印象里是好像还搞过那么一个诗刊,就是《银杏》诗刊。当时在这个诗刊之前,我们实际上就是学校的老师、学生聚在一起交流。在这之前有一个叫《云岭文札》的刊物,这个刊物在中文系的资料室里面应该有留存,它实际上是师生共同交流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觉得搞创作,还是要有这么一个刊物,当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时候诗社成立,你要说它在我印象当中是怎样的,银杏文学就是社以诗歌创作,尤其是现代诗创作为主的那么一个文学社团。
林:您当时是通过怎样的途径知道并加入银杏文学社的?是朋友邀请的还是一些其他的方式?
黑: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说的,我们出去郊游那些事。因为我当时也是刚进校没多久,这些学长们就来找到我跟我说,实际上就直接就约我了。学长是高年级的,那时候中文系四个年级的学生总共不到四百人,大概有两三百号学生。

yl6809永利官网81级部分学生同游翠湖(图片来源:蔡毅提供)
骆:您当时在银杏文学社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在社时期组织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黑:也没有特别具体的分工,参加活动有过那么几次,我记得好像还在至公堂搞过诗歌朗诵会。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于坚,还有他们班一个叫姜大才的同学。那几个师兄你们采访过他们吗?
骆:我们师姐已经采访过蔡毅老师、朱红东老师、文润生老师、张稼文老师。
黑:嗯嗯,我认识,文润生好像是在大理工作,你们跑大理去了?
林:不是,当时是通过邮箱进行线上采访的。
林:您的写作是从银杏文学社开始的还是在加入文学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找到了银杏文学社当时的一些杂志,但是没有在里面找到您的作品。
黑:写作的话,应该来说从高中开始还是有一些写作,但是都不入眼,都扔了,扔哪去都不知道。至于杂志,这个应该是后来的话了,实际上,我到了大二以后,就没怎么参加银杏文学社的活动,后来还跟师兄弟们都比较熟,有时候还在一块,但也是个别的交流多一些,正经八百的参加文学社的活动就不多了。
骆:我们看当时那些资料的时候发现您是中途脱社了,您当时脱社的原因是什么?
黑:大概在大二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没多少才情吧。到了大学才发现,如果要是搞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文学这一块,自己还有很多的书没读过,于是我更多的时间就花在读书上了,大家在一块搞活动什么的,我都不大参加了。
林:那您当时上学的时候读的比较多的是谁的作品?
黑:当时上学的时候,差不多从大二开始,我就一头就扎进故纸堆里去了。我就是读先秦两汉文学、外国文学,可能19世纪欧洲文学读得比较多。我毕业以后去考川大的研究生,当时有一个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一个老专家,我去考他的研究生,但没考上。
林:那个时候招的人都很少,好像几年才招一次。所以您是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吗?
黑:古典文学这一块我学习的比较多一点,像语言学、文字学,包括到后来小学这方面花的功夫比较多一点,比如训诂学、音韵学这些。当时是三年级就开这些专业课提供给我们就选修。训诂学我记得中文系有一个刘祚行老先生,当时他已经有五十多了,给我们上课。为什么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呢?因为读古代文献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些问题,你就得去深究。像训诂方面的、音韵方面的,遇到这些问题你要去解决,然后我就一头扎进了这个故纸堆里了。以后,包括到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论文都是写的有关庄子的。研究文艺理论,会更偏向于哲学美学一方面。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映秋院(图片来源:王雷提供)
林:除了银杏之外?您平时还会不会参加其他学校组织的文学活动?
黑:我进校以后当过中文系学生会的干部,就协助系里编《云岭文札》,好像编过几期,可能算是文学活动,就这些了。
林:您当时在银杏文学社的时候,哪些社员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黑:这个倒是可以说说。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后来我们也有过联络的,包括于坚、朱红东、蔡毅,姜大才是84年毕业的,毕业以后就基本上没见过,就没怎么联系了。我记得81级还有赵小晋、刘建国、张庆利、刘淑娟几个师兄师姐。当时写诗写得比较投入一点的,像82级的还有文润生和张稼文,他们俩写得多一点。我们这一届到现在还在写诗的有高专。还有后来当过文学社社长的熊伟,也是我们班的。
林:那你们平时会经常在一起交流讨论吗?
黑:我就是因为跟他们交流少了,成天就扎在图书馆里面读书去了,自然而然的就算是脱社了吧。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图书馆(图片源于网络,https://lib.ynu.edu.cn/sites/default/files/styles/1200_800/public/bgfc/%E4%B8%9C%E9%99%86%E6%A0%A1%E5%8C%BA%E5%9B%BE%E4%B9%A6%E9%A6%86.jpg)
林:那您现在和哪些社员的联系还比较密切的?
黑:倪涛,我们俩联系多一些。这十来年,偶尔还见一下于坚,因为于坚他夫人是我的同班同学,然后钱映紫、蔡毅。好多同学基本上都十多年没见了。倪涛呢,我们俩经常通电话,原来我们俩在一个单位,广播电视台。
林:您跟倪涛老师在文学社的时候就认识了吗?
黑:不认识,后来工作了才认识。他86级,他入学的时候我都要毕业了,当时在文学社的时候是不认识的。
林:那当时您和倪涛老师是怎么谈起都曾在过文学社的这一段经历的?
黑:银杏文学社当时在云南的综合院校,甚至于在医学院、昆工都是很有影响的。后来还在其他学校建过一些分社的,我记得医学院还是昆工建了第一个银杏文学社的分社。因为师大也有好几个,当时搞文学创作的好像还有师范学院的姚霏他们几个,还有民大的岳丁,景颇族的一个诗人,也受过银杏文学社的影响。
林:那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您再回想当时在银杏文学社的时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黑:那个年代,人都比较纯粹。诗社的氛围,跟我们国家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是分不开的,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没多久,大家该挣钱的都上街去摆地摊去了。那么在学校里边的我们就好好念书,好好的搞自己的事情,搞创作也好,念书也好,都是那么一回事儿,也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还出去兼职。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或者说就从文学本身来讲,创作也好,或者是搞研究也好,大家都是全身心的去投入文学的学习实践当中。还有包括生活各方面来讲,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很纯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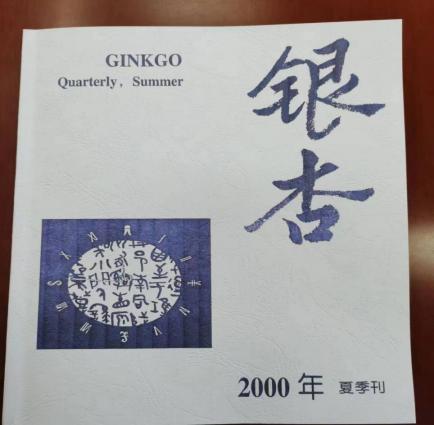
银杏文学社书影(图片来源:谢竺轩提供)
林:您现在看书会看哪方面的?
黑:我现在读的比较杂,应该是哲学类的。这几年我主要还是读有关《易经》方面的,相对来说读得比较多一些的就是中国哲学。因为没有集中的时间,顶多就是有时候歇下来了,可以有点时间翻两本书。我现在搞的是政策研究,为了做好工作,也得学很多东西。
林:您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现当代的作家或者作品?
黑:当代的作品读得比较多一点的,就是当时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些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持续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也都还在读他们的作品,包括舒婷、琼瑶、贾平凹、莫言等等,还有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这些都读。可能更喜欢读的还是金庸的作品。
林:之前就是看一个文学评论家说老师上课的时候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会说读卡夫卡,但实际上卡夫卡的书通常翻看两页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了,但是看金庸的话就可以看一整个晚上。
黑:卡夫卡,在当时世界文学这一块是读过的,但对我的影响不大。学欧洲文学的时候,重点还是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一块。当然,当代西方文学当中也还是会去读一些,但基本上读的也是当时比较前卫的,比如说《百年孤独》。还有包括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作家,还是偏现实主义的多一点,现代派的就读的少一点。书太多,只恨时间少,记得那会儿我们忙不过来读那些大部头的欧洲文学作品,学校在四合院有个电教室,我们就去电教室看电影,就是原版的当时也还没翻译过来,像什么《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这些,看了几十部,那个电教室里面都有,只允许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学生去看。
林:您当时读作品,一般是您自己去图书馆找,还是老师会给推荐一些?
黑:我跟其他同学学习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自己读书方面的积累太差了,进了大学才觉得该读的东西太多。其他同学可能老师会要求,老师在课堂上会要求说是这本书,下一周或者下个月要讲,涉及到的作品你们都读一读。老师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就会到图书馆去抱一摞回来。当时我们大概一次可以借5本书吧,我们每个人有5张借书卡,一张卡一面有20栏,可以借20本,两面就是40本,5张一共就是就是200本,我记得大概在大二,我的那批借书卡就全部用完了。
林:您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有没有对哪位老师的印象特别深刻的,觉得他讲课讲得很好,课很有趣的?
黑:课特别有趣?我觉得可能讲课讲的比较好的话,印象比较深的应该就是我们讲古典文学的几个老师,一个是讲唐宋部分的殷光熹老师;还有一个是冯明叔老师,那会儿都已经六十多了;有一个是讲诗词格律的吴进仁老师,他肚子里边诗可多了,据说他能够背九千多首古诗词。

殷光熹老师,(图片源于网络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E%B7%E5%85%89%E7%86%B9/5824149)
林:那您对现当代文学有印象比较深的老师吗?
黑:现代文学,也是比较有印象,像我们讲现代汉语的,有一个叫杨一兵老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她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也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有一个,就是后来调到到上海大学还是复旦的薛才德老师,他是上海知青,教语言学,我语言学当中的国际音标,就是跟着他学的。
林:我们发现您好像更喜欢偏古典的。
黑:是有一点。能够静下来读一本书,还是挺好的一件事。
林:我们还看了您的朋友圈,里面展示了一些您的书法作品,您现在的兴趣是转向了这方面吗?
黑:那些都是我茶余饭后弄的。工作了,也没有专门的时间去弄这些东西。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老师,就是张文勋先生。进校的时候,文勋先生是系主任,他没有任过我们的任课老师,但是后来一直都比较熟悉。我们当时那些老先生都是很关心学生的。那个时候晚上自习,自习室的那个教室里边大概是九点关灯,上完自习我们就跑去冯老师、殷光熹老师,还有文勋先生他们家里面去聊天。学中文,靠的是个悟,是老师在跟你的交流当中潜移默化地给你一种价值观,然后你就自己去跟着走。到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的时候,文勋先生他出了一个毕业论文题,有关庄子美学的,我选了他的课题,那是文勋先生最后一次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当时文勋先生笑称“红兵就是我本科的关门弟子了”。那个课题比较难,文勋先生指导我写论文非常的细致,真是花了半年时间,《庄子》我读了三个版本,然后才开始动笔写的。我为什么更多的对音韵学、训诂学,包括版本学这一些东西感兴趣?就是因为读了很多东西之后,发现这些工具必须得用的,就要去钻研它。文勋先生最终给了我的毕业论文一个“优”评。
林:之前看资料的时候,就有说当时的学生都会直接去到张文勋老师他们家里面,人很多,挤都挤不下。
黑:是的。文勋老师家的师母都认识我了,或许是因为我的名字好记。我爱人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她的名字也很特别,我们俩一班,名字又都很特别,所以师母也都记得。文勋先生他今年应该是九十岁了。

张文勋撰写《新建yl6809永利官网图书馆碑记》(图片来源:王云杉提供)
林:有的,前段时间文勋先生还接受了学校的采访,上面写的是九十六岁,看上去还精神特别好。
黑:是的,应该有九十六了。大概是2014年春节前,我去看文勋先生,买了两盆蕙兰送给他。先生非常高兴,说:哎呀,红兵怎么知道我喜欢兰花呢?我说:先生,只有这个花最合适您了。他说:我最喜欢了。文勋先生送了我一套自己写的书。先生说:“我就把这套书给你留个纪念。”因为当时他的眼睛也看不见,文勋就这么闭着眼睛在书上给我写的留言。文勋先生的夫人已经不在好多年了,他们俩对我都非常好。

黑红兵老师与采访者合影(图片来源:林娟提供)

